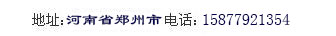序言提建议是一项冒险的行为。我深知这一点,因为我曾收到许多糟糕的建议,也几乎不可避免地给他人提过差劲的建议。在哈佛执教法律的三十七年时间里,我被要求给他人提建议的情形已不下数千次。大多数建言者只是在指导别人如何成为自己。人们似乎有一种重塑自我的强烈需求(也许这就是我们如此担忧克隆技术的原因)。我清楚地记得,我的一位身为杰出教授的导师告诉过我应按照何种顺序发表当时正在构思的论文。后来,我很快就明白了,原来他是在重述自己的出版经历。他想让我步他的后尘,其他几位导师也曾这样做过。我曾为其担任书记员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亚瑟·古德博格(AnhurGoldberg)总是劝我做一名法官,其实我并不向往这种职业。我在法学院时的导师约瑟夫·古德斯泰因(JosephGoldstein)教授则敦促我专注于学术和理论研究,但我喜欢涉足喧嚣的法律和政治实务领域。我坚信,模仿并不是恭维他人的最好方式,因为真正有个性的人是永远都无法被模仿的。慎重选择偶像PickYourHeroesCarefully律师更容易崇拜英雄。也许是因为善与恶在我们这一行里并非总是泾渭分明吧,我们需要创造出富有英雄色彩的偶像来顶礼膜拜。我们将英雄身上的缺点粉饰起来,把他们装扮成不犯错误的圣人。结果,我们还是了解到真相,即便不是大失所望,也会有些许失落。由于已经不止一次地有过这种感受,我自然懂得其中的道理。我心目中曾经的法律英雄包括克莱伦斯-丹诺(ClarenceDarrow)、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WendellHolmes)、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Brandeis)、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Frankfurter)、雨果-布莱克(HugoBlack)、威廉-道格拉斯(WilliamO.Douglas)、瑟古德-马歇尔(ThurgoodMarshall)以及威廉-布伦南(WilliamBrennan)。此外,还有大卫-拜兹隆(DavidBazelon)和亚瑟-古德博格(ArthurGoldberg)两位法官,我曾为他们做过书记员。我在耶鲁时的几位法学教授以及哈佛的几位年长同事也位列其中。我曾经希望自己成为像这些法学巨擘一样的人。在我成长的社区和家庭环境里鲜有法官或律师。我清楚地记得曾请求移民到美国的奶奶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拜伦考夫法官。她问我为何要见拜伦考夫法官。我告诉她,因为他是法官。奶奶大笑,她说拜伦考夫是个屠夫。“那你为什么总是管他叫法官呢?”“因为他就叫这个名字。法官-GEORGE。”在英语里,“法官”一词的发音与“乔治”较接近,作者的祖母将“乔治”误读为“法官”——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注,下同。奶奶用她浓重的意第绪一些欧洲犹太人使用的语言。口音拼出他的名字。在老布鲁克林的邻居中,拜伦考夫“法官”让我有了近距离接触真实法官的幻觉。所以,我四处寻觅我的偶像,并在这些法官、执业律师和法学教授中找到了我的偶像——他们中有些仍然健在,有些则已经乘鹤西去。我尽可能地通过阅读去了解那些已经仙逝的偶像。在我上学的时候,法律人的传记大多像是为圣人作传。我成长在一个为大多数公众人物歌功颂德的时代。当时,克莱伦斯-丹诺在《为救赎而辩》(AttorneyfortheDamned)中被美化。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来自奥林匹亚的美国佬》(YankeefromOlympus)中被塑造成一个光辉的形象。托马斯-莫尔(ThomasMore)则成了歌剧《公正的人》(AManforAllSeasons)中的男主角。在百老汇,我看到影星保罗-穆尼(PaulMuni)在《承受清风》(InherittheWind)又译《向上帝挑战》。中扮演的伟大律师克莱伦斯-丹诺,那一天令我终生难忘。当我观看“丹诺”(他在剧中被称作“德拉蒙德”)对“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特”(剧中的“布莱迪”)的质证时,我明白了自己想要成为什么样的律师,应该成为什么样的律师。但许多年后的一天,我首次听说丹诺为了在刑事案件中赢得无罪判决或使陪审团无法形成一致意见,曾行贿证人和陪审员,这几乎是确凿无疑的。这一天同样令我无法忘记。我简直崩溃了。心目中的英雄不仅是个泥足巨人,他的高大形象已在我面前轰然倒塌。曾有人请我为杰弗里-科万(GeoffreyCowan)关于丹诺的新书写一篇评论。这位作者对他书中的主人公充满了同情,在他列举的案件中,大公司不惜重金收买判定工会有罪的裁决,丹诺为了与这些公司平等竞争不得不行贿。这无法说服我。无论动机如何,行贿陪审员的铁证使丹诺永远与律师的偶像无缘。即使是为了与对手公平竞争,也没有任何道理去玷污法律制度。在他的书中,科万写道,法学院并不传授行贿这样的技巧。对于这一点,我在评论中对此表示赞同:我们之所以不在法学院里教这样的技巧是因为它们不应是律师使用的手段。它们事实上也许是革命者或其他体制外人士使用的手段,他们为达到目的甚至可能通过革命的方式使其正当化。但作为从事法律工作的律师,无论面对怎样的挑衅,都不能运用这样的手段。律师可以去抱怨、揭露或者谴责对手的腐败行径。甚至只要理由正当,对方的行径的确令人愤慨,他可以改行成为一名革命者。但律师就是不能为了赢得正义而以律师的身份干起腐败的勾当。如果丹诺果真像科万确信的那样跨越了这条鸿沟,那么他便不配笼罩在头上近一个世纪的光环。在了解到丹诺的污点后,我们这些长久以来将其视为英雄的人难免失望,但是,残酷的历史真相永远比带有浓重感情色彩的圣人传记更有分量,哪怕主人公是为数不多的律师出身的法律圣人。然而,这些文绉绉的话语还是掩盖了一种不愿言说的失望,甚至是悲伤。与《卡萨布兰卡》里那位听说里克酒吧里有赌局便故作惊诧的警长不同,我可是实实在在地深感震惊。这种情绪持续了好几周。丹诺欺骗了我,让我以他那样的律师为榜样,这使我深受折磨。尽管丹诺早已辞世,但我对他的怨恨还是那样真切,那种感觉就像怨恨一个背叛了自己的密友或恋人,久久不能释怀。后来,当我得知其他偶像也大都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瑕疵时,我就不那么情绪化了。幻灭的过程是缓慢的。当发现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在给朋友的私人信件中所阐述的价值观是何等恐怖时,我并没有立刻感到失落。他赞成对“低能儿”实施绝育——甚至可能是谋杀。霍姆斯在信中同意处死“任何不合格的人”,并且“将经检查不合格的婴儿杀掉”1。在承认强制绝育法律的合宪性时,他赞成对一个被误认为“低能儿”的女性实施绝育手术。按照霍姆斯确立的这个先例,成千上万的人们被实施绝育手术,而他们中有许多人是被误诊的。甚至连纳粹也引用过该判决用以支持他们的种族优生计划。我在哈佛目前所担任的正是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当年的职位。当我读到他曾在大屠杀期间拒绝帮助欧洲犹太人时,真是怒火中烧。但当时我已经接触过弗兰克福特大法官,并且不喜欢他的为人——小气而谄媚,因此也就不那么失望了。但对于布莱克大法官,情况则有所不同。据我所知,他在升迁至高等法院之前曾加入三K党,但我认为他已经摒弃了早年的种族主义。后来,就在我到最高法院担任书记员那年,遇到他对一群书记员发表讲话,他那根深蒂固的种族偏见还是表现得很明显。他的固执己见、排斥新观念也给我留下深刻印象。道格拉斯大法官倒是乐于接纳新思想,可他对书记员、秘书和其他法院工作人员的态度却很恶劣。他还与我的上司大卫-拜兹隆法官发生过争执,其表现令我甚为惊讶。当时,有人请拜兹隆法官到道格拉斯参加的一个私人俱乐部发表演讲。该俱乐部将犹太人和黑人排除在外。身为犹太人的拜兹隆拒绝了邀请,他说不能去一个他自己或其他人没有资格参加的俱乐部演讲。道格拉斯打来电话,斥责他“思想狭隘”。拜兹隆示意我拿起另一个听筒,听他的讲话。我当时简直不敢相信我所听到的一切。就是这位倡导种族和宗教平等的楷模,力劝我的上司作出妥协,到那个种族隔离的俱乐部去演讲。拜兹隆坚持己见,道格拉斯则怒气冲冲地摔了话筒。我的其他几位偶像:路易斯-布兰代斯、瑟古德-马歇尔和威廉-布伦南,都有一些不太严重的缺点,但每当我得知后还是有些失望。布兰代斯的行为有些不太符合律师的职业伦理,因为他有时将自己视为“天下人的律师”,而不是为某个特定客户而辩。马歇尔对案件辩论的准备经常不够充分,即使是对最高法院的重要案件也是如此。布伦南在很多年里一直拒绝雇用女书记员,而且曾在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Warren)的坚持下解雇了一名书记员。当时,这位书记员所从事的左翼活动成为各媒体报道的主题。尽管明知这三位法官并非完美无瑕,但我还是非常敬重他们。我曾为其工作过的两位法官也同样如此。当你同某个人朝夕相处时,他们身上的优缺点就会显而易见。正如一则古老的英谚所云:“没有谁会成为他的管家心中的英雄。”也没有哪个法官会成为他的书记员心中完美无缺的圣人。但是,在诸多重要方面,大卫-拜兹隆法官和亚瑟-古德博格大法官仍然是我并非尽善尽美的偶像,我的几位教授和年长的同事也是如此。所以,没有偶像,也不要崇拜偶像。你可以去仰慕拥有可敬之处的人们,但要明白,人人都有缺点,有些人的缺点还要更多一些。失望是在所难免的,尤其是当你得知那些曾令你仰慕的人的缺点时。学会坦然面对失望吧,而且仍要学习你的偶像身上那些值得学习的特点。然而,即便是单独的一个特点也很少是没有半点瑕疵的。法律不是一个完美的专业,不牺牲某些原则往往难以取得成功2。因此,所有的执业律师,以及该行业中的其他大多数人士,必然是不完美的,在那些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眼中就更是如此。正如不存在绝对道德一样,也不存在绝对的正义。但绝对的不公正却是现实存在的,而且让我们一见便知。我现在只能想象,当众多对最高法院大法官无限崇敬的法学院学生们意识到,五位大法官违背誓词,在年大选中阻止佛罗里达州的手动计票时会作何反应。法官宣誓要求每一位法官“主持正义、一视同仁……”尽管作出上述宣誓,五位法官还是完全无视他们之前所作的判决,停止了计票以便确保一个特定当事人——小布什的当选。如果在同样条件下停止计票的结果是戈尔当选,那么他们绝不会这样做。如果不相信,可以思考下面这个法学院模拟案例。假设在这次选案发生前的六个月,一千名最杰出的宪法学教授、最高法院律师和报道高等法院新闻的记者们已经获知佛州案的大致案情,唯一的不同是,没有提供当事人姓名和他们所属的党派。会有人认为专家们将预测出那五位法官将如何终止投票吗?相反,大多数人都会根据法官们之前的判决预测到,首席大法官威廉-伦奎斯特(WilliamRehnquist)和大法官安东尼-斯卡利亚(AntoninScalia)、克拉伦斯-托马斯(ClarenceThomas)和桑德拉-戴-奥康纳(SandraDayOConnor)最不可能加入这样的判决。毕竟,这些法官曾不止一次地作出裁决,认为州政府根据远不够精确的标准处决谋杀犯时并未违反平等保护条款指美国宪法第14项修正案,要求各州“在其管辖范围内,不得拒绝给予任何人以法律的平等保护。”。如果戈尔副总统当时已经领先几百张选票,而布什州长要求重新计票,我敢说这些法官将拒绝戈尔提出的平等保护请求。如果我说的没错,这不是区别对待又是什么呢?根据个人或政党的不同,根据当事人的党派来作出判决,这违反了审判的首要原则。法官不得在案件审判中偏袒任何一方。P.我曾在其他作品中详细探讨过该判决3。而在本书中,我的思考角度有些不同,想谈一谈当得知某些法官事实上在行骗后产生的极度失望情绪。也许,你也曾怀疑过,某些地方法院法官偏袒那些支持他们当选或任命的律师和当事人。但最高法院的法官也会如此吗?对于像我这样一辈子愤世嫉俗的人,这也足以令人震惊了。这对于你对法治的信仰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是否让你有了行骗的充分理由?我希望上述事实能进一步加强你对法治和法治实践中绝对诚实的信仰。它还应该让你对法律或司法机构持一种更加怀疑的态度。不要相信任何掌权者,特别是法官。不要被司法意见的表象所迷惑。回去认真读一读,仔细研究一番案件,你就会惊叹于法官如此频繁地运用手腕儿操控案情和法律。这种情况太常见了,即使是长期对司法界有异议的人士也将其看作是某个法官的学术诚信问题。若想有所改善,就只能靠你自己了。如果你察觉到违法违规行为,就去司法会议、律师协会或议会举报。同时,一定要保证你对他人的批评确切无疑,以防遭到违反职业行为的指控(千万要记住,法官和律师是官官相护的)。与此同时,还要现实一点。要知道,法官也是人。在美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能走到今天这一步,靠的就是政党政治游戏,而其玩得还不错。对于司法界来说,最有力的制衡力量就是充满疑惑的法律服务消费者。而这支力量的培养必须从法学院开始,必须从你们中间开始。说了这么多,我必须承认,我的心中仍然有一位完美的偶像。他是一位律师,但是他的英雄气概主要体现在其职业领域以外。我甚至还同他接触过,对他有所了解,但他在我心中的英雄形象丝毫没有减损。他的名字不太广为人知,他的英雄事迹也绝不会被复制——至少我不希望这样。他叫詹-卡斯基(JanKarski),年7月逝世,享年86岁。当他28岁那年在波兰担任律师和外交官时,这位天主教学校的年轻毕业生为了报告恐怖甚至是致命的情况,悄悄潜入犹太人区和死亡集中营。他被盖世太保俘获,受尽折磨。逃脱出来后,他又一次冒着生命危险重返集中营。为了改变外貌以便避免盘查,他拔掉了自己的牙。通过揭露在纳粹占领下的波兰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也许本可以拯救成千上万人的生命。然而,当他带着他的详细信息从波兰偷渡出来后,他被引荐给当时在华盛顿最重要的犹太人:与罗斯福总统关系甚密的大法官菲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卡斯基凭借一名伟大律师对细节的记忆,向大法官汇报了他在犹太人区和集中营的详细见闻。弗兰克福特拒绝将这些信息报告给罗斯福总统,他说他不相信卡斯基的报告。现实情况却是,弗兰克福特不想将自己的可信度压在一份罗斯福不太可能相信的报告上,从而影响他们之间的友谊以及他的影响力。这就是一个真英雄和一个有瑕疵的大人物之间的差距。请理解这种差距并学会接受它。激情点亮人生LivethePassionofYourTimes我们不要把激情保留在卧室里,而应将其延伸至整个职业生涯中。被投入到工作中的时间和精力将远远多于男欢女爱,或者健身、美味和听歌剧。然而,对律师建议却通常是平心静气、不偏不倚、客观、超然——总之,要表现出专业性。其实,只要对二者运用得当,激情和专业性并非水火不容。激情是原动力,专业性则是完成任务的手段。即使这个手段要求客观、超然,激情仍可以激发出运用该手段的最佳方式。有时,你需要彰显自己的激情。成功的律师可以有选择、有节制地将激情作为辩护的工具。但不要滥用激情,否则它就会像喊着“狼来了”的孩子一样,自损效果。激情不仅在法律职业中具有价值,在生活中也是一股重要力量。我曾见过一些律师在工作中是如此超然、冷静、不温不火,以至于做任何事情都不再有激情。职业习惯已然占领了他们的生活领地。吉尔伯特(Gilbert)和沙利文(Sullivan)在其《天皇》(Mikado)一书中谴责了那些只对过去歌功颂德的人。诗人爱德华?阿灵顿?罗宾逊(EdwardArlingtonRobinson)创造了迷尼弗?契维(MiniverCheevy)——一个“对过去无限留恋、慨叹今不如昔”的形象。许多人试图在科幻小说、历史和传奇故事中逃避现实。霍姆斯大法官鼓励他的律师同行们要活出激情,这毫无疑问是正确的。有句中国古代俗语说:“宁为太平犬,不做乱世人。”对于我来说,这从来都是一句祝福。除非遇到大屠杀这样的乱世,每个人都可以饶有趣味或按部就班地生活。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态度问题。最近,我从曾经教过的一位学生那里收到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他在信中直接谈到了这个话题。经其允许,我将其中的一部分摘录如下:尊敬的德肖维茨教授:大约六年前,我很幸运地拥有您这样一位刑法学教授。也许您已经从信头猜出来,我在从哈佛毕业后并没有继续从事刑法方面的工作。然而,我却听从了您在课堂上反复向我们传授的建议:在自己热爱的领域继续闯出一条道路(我最终选择了劳动法领域)。当您最初鼓励我们开辟自己的职业道路时,我并不太确定您的建议是否适合我。我知道我很有可能去一家大型律所,而且刚一开始做的都是合伙人直接指派给我案件。但当我最终走进波特莱特律师事务所(PorterWright)时,我决定努力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因为在我开始工作的每一天里,这家律所就像您当初在课堂上一样激发着我的进取心:做律师是件多么激动人心的事情。几个月以前,一位同事让我说出在哈佛法学院里我最喜欢的教授。我有很多喜爱的教授,朋友对我的大多数答案并没有感到意外。但是,当我提起您的时候,这位朋友(他没有听过您的课)皱起了眉头。他知道我在政治上较为保守,我想他因为我选择了一位与自己政见大相径庭的人而吃了一惊。但是我选择您的理由与您的政治观点毫不相干。正如我向朋友解释的那样,我从您那里得到了哈佛法学院教授中最好的建议。而且,与其他教授不同,您每一天都在表现出您是如此挚爱律师这个职业。(和办公室里每天收到的那些充满怨恨的信相比,这封友善的来信太不一样了。那些形形色色的来信者或癫狂的、或固执、或怒不可遏,许多信的内容都登不得大雅之堂。最近有一封还可以拿到台面儿的信,写信人是一位哈佛校友,他并不是我的学生。他说我让人想起了“伍迪?艾伦WoodyAllen,20世纪后半期美国重要的电影导演和喜剧演员,影片中的角色通常是自我